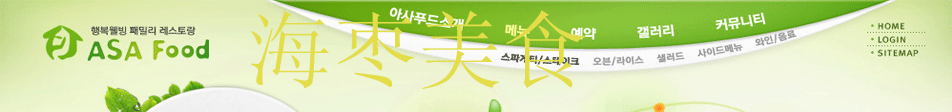|
精彩内容 前文讲到南平王钟传始建蟠龙寺的缘起及时间,以及可文禅师与令超禅师和蟠龙寺之间的佛缘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了解到“和光重建蟠龙寺中兴”之因缘北京,还有夏后娘娘与蟠龙寺发生的感人故事哦~ 宜春历史文化研究会《蟠龙寺千年流变研究》课题组 主持:刘密 执笔:甘也达 成员:刘密甘也达邹峰杨晓东张逸珉林梅芳释本耆 龙门关 三蟠龙寺在唐末江西钟氏割据政权覆亡以后便开始衰落,历经五代十国,入宋百余年史乘灯录诸文献鲜有记载,法系难考。不过,正德《袁州府志》载“宋治平间赐额‘永庆’”(见该书卷之五寺观5叶),说明宋英宗赵曙治平年间(—)蟠龙寺仍在,而且还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否则朝廷不会赐额改称“永庆寺”。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例如寺中未出值得一书的高僧,),未能进入北宋禅僧道元的视界,因而未载入成书于宋真宗景德元年()的《景德传灯录》。直至南宋初年,作为“普庵嫡子牧庵孙”的和光禅师重建梵宇,蟠龙寺始中兴再度辉煌。 同治《宜春县志》载:“蟠龙禅院,和光祖师道场也,师姓李,石里乡钟家岭人。相传为普庵弟子。”(见该书卷十杂类15叶)石里乡即今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续灯正统》列有慈化普庵印肃禅师法嗣四人,其中就有“盘龙和光世禅师”。(见该书目录)但正文无传无语录,生平事迹灯录无考。说和光必说普庵。普庵印肃禅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颇有灵异如济颠的禅僧。《普祖灵验记》述其灵迹颇多。然而拨开灵异的神光,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大德高僧。普庵深谙即心即佛、道由心悟之禅理,且颇有超佛越祖之气度。某日阅《华严经》至“达本情忘知心体合”处,豁然大悟,曰:“我今亲契华严境界矣!”普庵虽为禅僧,却能融摄华严法理,是为大智慧。普庵布衣菲食,励精行道。“凡四方慕道来者,师随机引诱;其以灾患疾苦请,或书颂,或□水与之,无不立验。”(同治《宜春县志》卷十杂类10叶)宋孝宗乾道二年,普庵创建慈化寺于南泉山,“不数载,梵宇金碧,如从天降”(见《续灯正统》卷六)。由元入明,盛极一时,明成祖朱棣敕书“天下第一禅林”,因号称“天下大慈化”。诚普庵祖师之大功徳也。 和光乃普庵祖师亲自点化之得法弟子。《普祖灵验记》载有“师度和光”事。和光禅师姓李名和,或称李光和,与普庵禅师同为宜春石里乡人。据《南泉慈化寺志》年谱品载,和光禅师生于宋高宗绍兴四年()甲寅八月。(见该书上卷54叶)方志言其“为学博”,乡试中举为解元。宋孝宗乾道(—)初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李光和踌躇满志,赴东京赶考会试,乘驴行至高陂桥遇普庵禅师,礼貌不恭。普庵以一二偈语挑之,曰:“选官固高,何如选佛?”光和遂有所悟。与普庵言谈相契,“顿兴慕道之心,尽灰功名之念”,并发誓随从普庵出家。普庵知其家有妻子,劝其“且作在家菩萨”,为其更名曰“和光”,字应世。但和光却说:“学道不归家,归家道不成。”(《普祖灵验记》一册47叶)表明虔诚皈依礼佛之意。这“选官”“选佛”之说,古已有之。唐代有一五泄和尚,原本是个秀才,打算“入京选官去”,为马祖道一禅师点化而出家具戒。(《祖堂集》卷第十五)马祖另有弟子邓州丹霞天然禅师,初习儒学,将入长安赴试。路上偶遇一禅客劝曰:“选官何如选佛?”并告之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见《景德传灯录》卷十四)这“选佛”俨然在与“选官”争生员。古代选官而无成者,不在少数;选佛而有缘受大德高僧点拨者,亦非多数。和光摄受具戒于普庵,可谓缘份不浅。 普庵似乎对和光早有预期和安排。某日和光问师曰:“某出家于道,果有分不?”师曰:“异日到九十九湾,遇蛇则往,逢龙则止。”又在桌上书“马生角”三字示之,指以南行。后来和光禅师南行止宿于骆姓妈妈家,始悟“马生角”之意。次日早上登山遇蛇引路,屈曲而上,“到蟠龙关,遂于此立寺建道场,其道大播”。这道场便是蟠龙禅寺。此为《普祖灵验记》版本。(见该书47—48叶)同治《宜春县志》版本则言普庵所授秘符为“遇桥即止,遇龙即住”。下述:“师由是杖锡而南,徘徊大仰、木平歧路之间,至虹桥而止。遇一蛇,翘首折行。师随至蟠龙山下,蜿蜒而上,抵绝顶,蛇因蟠而伏焉。师即其地为禅室。蟠龙盖以蛇得名也。”(见该书卷十杂类15叶)宜春方言“虹”“绛”音同,“虹桥”即今宜春洪江绛桥。蟠龙山在绛桥东南约二里路处。二说有诸多不同,前说重在发扬佛法,后说重在考据故实。但都肯定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和光禅师在普庵祖师所授秘谶指引下前往袁州绛桥蟠龙山另建道场弘法。蟠龙寺由此中兴。 禅宗五家中沩仰宗入宋不传,法眼宗于宋初永明延寿后衰落,曹洞宗在北宋也影响不大。唯有临济宗和云门宗仍盛行各地,“四方谈禅者惟云门、临济二氏”(《避暑录话》)。特别是临济宗,在宋代得以长足发展,可谓禅门显学。临济宗属南禅洪州一系,开宗祖为临济义玄(?—)。慧能禅系历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至临济义玄而兴。南岳四世祖黄檗希运得奉新百丈山怀海禅师正传,于唐开成(—)年间到宜丰黄檗山驻锡传法,僧侣云集,其中就有义玄。义玄从希运学法三十三年后,往镇州(今河北正定)滹沱河畔建临济院,弘扬希运新法而大张天下,世称“临济宗”。临济宗五传入宋至石霜楚圆,发展规模日益扩大。石霜楚圆有弟子杨岐方会和黄龙慧南,而分头弘化出杨岐、黄龙二派,盛行于江南,禅门遂有“五宗七家”之说。杨岐方会禅师(—)初从石霜楚圆掌监院事,后住筠州九峰山,不久便栖止袁州宜春杨岐山(在今江西萍乡北)普通禅院,收徒传法,门庭繁茂,自成一派,是为“杨岐宗”。黄龙慧南用“三关”启悟学人,从轮回解脱的角度强调凡圣无别,生佛无二。而杨岐方会则融会临济、云门两派风格,以灵活的机锋棒喝或法语启发开示学人破除执著,自省自悟。尝言“莫道杨岐山势险,前头更有最高峰”。其机锋机语,巧言善辩,远胜慧南。黄龙派北宋末期开始衰落,南宋初便法系难考,杨岐派遂成为临济宗之正统。“黄龙派法脉断绝后,杨岐派恢复了临济宗的名称,代表着禅宗,一直传至当代。”[5]曹洞宗南宋初虽有起色,但其法脉远不及临济之盛。禅宗史上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正是在禅门临济宗几乎独步天下的大背景下,蟠龙寺中兴。 要之,蟠龙禅寺在南宋初南禅临济宗大盛“临天下”的背景下重建中兴。其开山祖袁州蟠龙山和光应世禅师(—?)属南岳临济宗杨岐一派。袁州杨岐方会禅师(—)传至舒州白云守端禅师(—),门庭极盛;再传至蕲州五祖法演禅师(—),而被誉为“中兴临济”。五祖法演门下得法弟子二十二人,有佛果克勤、佛眼清远、佛鉴慧懃所谓“三佛”者为其高足。其中舒州龙门佛眼清远禅师(—)传隆兴黄龙牧庵法忠禅师(—),再传袁州慈化普庵印肃禅师(—),复传袁州蟠龙和光禅师,故宋孝宗诗有“普庵嫡子牧庵孙”之句。蟠龙山和光禅师实为慈化寺普庵印肃禅师亲自点化之嫡传弟子。和光禅师在《续灯正统》目录中列为临济宗“大鉴下第十八世”,按《五灯会元》谱系即为“南岳下十七世”,按《禅灯世谱》世系图则为“南岳临济宗下十三世”。其师普庵禅师按世系图则应为“南岳临济宗下十二世”,而其师祖牧庵禅师按世系图则应为“南岳临济宗下十一世”。前述《续灯正统》目录列有普庵印肃祖师得法弟子四人,和光禅师为上首。其他三人为佛慧清禅师、铁牛礼禅师、衲僧俊禅师。其中衲僧绍俊禅师在《南泉慈化寺志》中列为慈化寺第十八代住持。 四蟠龙寺中兴,禅风远播,再度辉煌,又与南宋孝宗赵眘(—)之成恭夏皇后(—)有紧密关联。 《宋史?后妃传》载:“成恭夏皇后,袁州宜春人。曾祖令吉,为吉水簿。夏氏初入宫,为宪圣太后閤中侍御。普安郡王夫人郭氏薨,太后以夏氏赐王,封齐安郡夫人。即位,进贤妃。逾年,奉上皇命,立为皇后。”(《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夏氏入宫,先得太后青睐,再得孝宗宠幸,复得上皇钦点,终得“立为皇后”。虽非一步登天,但也无太多曲折。若非天生丽质,贤德聪慧,焉能得此荣宠?身为袁州宜春人的成恭夏皇后,未贵时家居今宜春市袁州区温汤镇夏家坊。成恭夏皇后芳名史无记载,宜春乡间呼为云姑。云姑出生时,“有异光穿室,父协奇之”。长大成年后,贤淑聪敏,姿容俱佳,于是在其父夏协(—)的调教张罗下“以姿纳宫中”。这一年为高宗绍兴二十三年(),云姑十七岁,夏协五十二岁。选女入宫固然荣幸,却是要打点尽人事的。夏氏入选后,夏协已家贫如洗,资财耗尽,“居益困,及归,客袁之僧舍,号夏翁”。(《宋史?后妃传》)这僧舍便是“袁之蟠龙僧舍”(正德《袁州府志》卷之九遗事6叶),即和光禅师在普庵禅师谶示下重建的袁州蟠龙寺之僧舍。夏翁穷困无路,幸得和光禅师收留,寄居蟠龙寺,靠施舍度日。夏翁送女入宫,当然希望有个好盼头。然而,“翁亡,后始贵”。隆兴元年()冬十月,“立贤妃夏氏为皇后”(《宋史?孝宗本纪》)。宋孝宗乾道二年(),夏皇后“谒家庙”,荣归宜春故里。不幸九年前夏翁已然亡故,葬于蟠龙寺东首。贵为皇后久居深宫十余年的昔日云姑,面对一抔黄土,自然痛极哀毁,难以自持。痛定之余便只有播撒雨露于乡里,以了未了之愿,“宗族亲属推恩者十一人”。其亡父夏协追赠太子太师,爵封信王;其弟夏执中补承信郎、閤门祗候,后累迁至奉国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加少保,封宜春侯;其他亲属也各有封赏。也许是哀毁过甚,一年后即乾道三年()夏皇后“崩”,册谥安恭;宁宗庆元年间(—)改谥成恭。后又推恩及蟠龙寺,宋孝宗淳熙年间(—)赐额,改称蟠龙寺为“报亲显庆寺”。正德《袁州府志》载:“报亲显庆禅寺:府城南集云乡蟠龙山顶,唐南平王钟传初建蟠龙禅院。宋治平间赐额‘永庆’,淳熙改赐今额,是为成恭皇后功德院。”(见该书卷之五寺观5叶)蟠龙禅寺遂进入再度辉煌时期。 蟠龙寺改名为“报亲显庆禅寺”,是在淳熙年间即夏皇后驾崩至少七年之后。何以迁延至此时?自有其故。宋孝宗赵眘(—)被认为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史称其“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宋史?孝宗本纪》)。期间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张浚,力主北伐,锐意收复中原;内政上积极整顿吏治,惩贪汰冗,轻徭薄赋;勉农桑,尽地利,重视农业生产,百姓富庶安乐,史称“乾淳之治”。宋孝宗为人“性恭俭”,励精图治,勤政爱民,事必躬亲,自称“蚤夜孜孜不敢怠惶”(《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宋高宗则赞其“勤俭过于古帝王”。他初登大宝,不肯用乐;常穿旧衣,日常花费不多,也不大兴土木;很少赏赐大臣,宫中收入多年未动,以致内库穿钱之绳都腐烂了。这样一位锐意进取、力图恢复而“性恭俭”的明君,自然不会把赐额建寺这类事列入即时要做的议事日程。既然如此,那么七年、十年甚或二十年后,何以要赐额改寺名呢?这或许与夏皇后之弟夏执中有关。夏皇后省亲,流落异地穷困潦倒的夏执中终于苦尽甘来,有了出头之日。夏执中虽然是靠着裙带关系加官晋爵的,却毫无皇亲国戚的骄纵之气。当夏皇后亲自出面劝他“出微时妻”而另行择配贵族之女时,“执中弗为动”,且高声朗诵东汉名臣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之语以对,而“后不能夺”;当“近戚争献珍玩”为太上皇赵构行庆寿礼时,他不作俗人之举,独书“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大字以献,而“高宗喜”;他担任馆伴副使与金国使节周旋时,毫不示弱,持弓“连射皆命中”,而“金人骇服”;当宋孝宗得知这位小舅子有德有才能文能武,准备征召重用他时,他却辞谢说:“他日无累陛下,保全足矣。”颇合中庸之道,而“人以此益贤之”。(《宋史?后妃传》)讲情义,有气节,不趋炎附势,有自知之明且有大局观念。看来这位来自宜春明月山下乡野山村的国舅爷口碑不错,并非凡庸等闲之辈,更非恃宠而骄的纨绔子弟。其淳朴敦厚,甚合孝宗脾性。《普祖灵验记》录有宋孝宗一首《御赞和光禅师》诗,曰:“和光道德播乾坤,吾舅何须要独尊。朕以明知伊出处,普庵嫡子牧庵孙。”宛然一副郎与舅讨说法的情状,论理中透出亲切,也透出对和光禅师的崇敬之情。后附说明,言此诗系应“奉国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臣夏执中请”而题。此外还赐赠了一把题有旧诗的御书扇,后复附言曰:“朕闻和光禅师之道四海共称,吾舅欲尊之。于是信笔以赞其像就,以淳熙十六年四月所书纨扇赐之。庶使慈风广播,为大施众生除热恼、得清凉耳!”(见该书二册题咏86叶)一口一个“舅”而出自天子之口,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我们可以设想,夏执中此前一定多次向宋孝宗谈起过当年与其父寄居宜春蟠龙寺时,如何得到和光禅师关照与资助之事;当然也会谈到和光禅师弘扬佛法“大施众生除热恼”诸善事。夏执中有情有义,知恩图报,这或许就感染了宋孝宗,于是欣然为和光禅师题赞赐扇,颂其“慈风广播”,表达尊仰之情。如果此设想不虚,那么,淳熙赐额改寺名或许也就是在此类情况下,为超度抚慰成恭夏皇后和信王夏协亡灵,显扬或感恩蟠龙寺和光功德而作出的追念还愿之举。其中也许还有“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的宪圣皇太后的一片慈心。前述“报亲”有“图报恩亲”之意,而“显庆”则应为“显扬慈善”或“彰显良善”之意。《说文?心部》:“庆(慶),行贺人也。从心,从夊。吉礼以鹿皮为贽,故从鹿省。”徐锴《系传》:“夊,行也。”段玉裁注:“谓心所喜而行也。”去祝贺别人必心有所喜,心有所善。故“庆”又有善、福诸义。《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为善。《易?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为福。故寺名“报亲显庆”,其义可理解为孝亲、向善、祈福。 蟠龙山上离龙门关不远处的路边,有两块摩崖题刻路碑。其一为宋淳熙十五年()所刻,碑文为:“召匠凿石,从三门外至关前北石路一带。”其二为宋宝祐四年()所刻,碑文为:“雇工修砌行路,自水口山起至龙门止。”[6]其中淳熙十五年路碑所述与淳熙年间(—)赐额改寺名情事隐隐相合。宋孝宗虽为一代英主,力主北伐,恢复中原,可惜如史论家所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张浚虽为抗金名将,然符离一败,遂有隆兴和议;虞允文虽为“任重之器”,然积劳成疾,终无所成。而宋高宗赵构虽退位当了太上皇,却时有掣肘。宋孝宗赵眘在位二十七年(—),至其退位前二年太上皇才驾鹤仙去。宋孝宗虽为高宗养子,却十分孝顺。宋淳熙十四年()高宗大行,宋孝宗“百日后尚进素膳,毁脊特甚”。(见《齐东野语》)史称孝宗之“孝”如仁宗之“仁”,“其无愧焉”。在太上皇的压力下,宋孝宗在“战”与“和”、明君与孝子之间左右徘徊。“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隙可乘。”(《宋史?孝宗本纪》)宋孝宗有志无从施展。淳熙十五年是宋孝宗退位前一年,锐气渐消的他正处于一种力不从心、心灰意冷的状态之中。人在此状态下易于思旧,加上国舅爷夏执中有意无意的叙旧忆旧,此时赐额改名应该是个不错的适当时机。考虑到赐额与修路往往前后相续,我们且将宋孝宗赵眘为蟠龙寺赐额改名“报亲显庆禅寺”的具体时间定为“约宋淳熙十五年(约)”,即夏后崩后约二十一年。 宋孝宗“性恭俭”,不大兴土木。但淳熙赐额改名后,凿石修砌山路、小规模扩建殿堂亭阁、整修妆饰拱柱金身,或许还是会有的。蟠龙山报亲显庆禅寺遗址坐落于山顶一处盆地内,中间地平如掌,四面山峦迭起如莲花盛开。据遗址估测庙宇面积有四五百平方米,依山而建,风水极佳。前引南宋诗人张嗣古《蟠龙山》诗有“飞甍金碧悬山巅”、“纷纷冠盖趋尘埃”句,所描写的应该就是“淳熙改赐今额”建新葺旧、妆金饰彩后的报亲显庆禅寺。栋宇飞檐,金饰碧瓦,佛殿高耸,宏伟庄严;官绅士子,紫袍红巾,车盖纷趋,旌尘飞扬。从中可以想见彼时蟠龙山报亲显庆寺前一派香火缭绕、俯仰礼拜、熙来攘往的繁盛景象。 源于天竺的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土,便开始了中国化进程。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明进入中国,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发生矛盾与冲突。有学者认为,佛教在汉代被方术化,在魏晋被玄学化,历经南北朝至隋唐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到了宋代而达到高峰,可以说是佛教儒学化。有宋一代金兵屡屡南侵,极大地压缩了汉民族的地理空间,却大大地扩充了汉民族的精神空间,使宋人的民族意识、忠君爱国精神空前突显。宋代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强化,儒学复兴,佛教受到挤压。为了争取发展空间,佛教作出了更大的调适和妥协。宋代的不少名僧不仅把佛教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五戒”比作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常”,而且还大讲“孝道”。[7]北宋云门宗僧契嵩著《辅教编》设《孝论》12章“拟儒《孝经》发明佛意”,说:“孝出于善,而人皆有善心。”认为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都是为了行善、求善;且佛教之孝遍及众生,乃孝之“大本”。[8]宋天台宗僧智圆认为:“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宋临济宗僧大慧宗杲则认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故提倡忠君孝亲,说:“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9]前述普庵祖师在和光开悟誓言出家时说:“汝有妻子,且作在家菩萨”,命回了“当家缘”,所顾及的也是一种从家庭伦理出发的孝观念。又尝言:“舍家出家,当为何事?披缁削发,本属何因?若不报国资家,虚负皇恩;若不导化檀那,枉作释子。”把儒家的忠孝观念置于佛教戒律之上,佛教由此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条件。其儒学化的思路是“佛性(善):孝亲——忠君——报国——向善、积善、行善”。蟠龙寺改名为“报亲显庆寺”,正反映了宋代佛教儒学化的这一新特点。 待续··· END 禅宗圣地——宜春 金戈铁马红旗猎猎——从宜春走出的新四军 黄颇为何不是状元? 宜春城名之由来 剪纸话宜春 袁京与袁州 ————禅月宜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