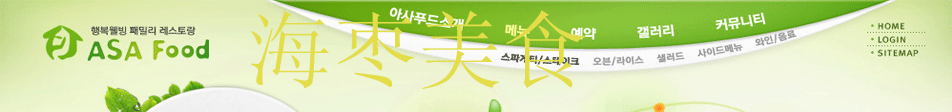|
1、何为地方感 何为地方感? 用一句话概括,地方感是指人对特定地域发生的情感依附与心理认同。 因而有三个元素构成地方感:人,地域,感知。 很显然,地方感中的感知即是感受,也是认知,是对具体的山水、人文、街巷、人物的深刻印象。有四个特征--- 整体性。地方感是整个地域全部特征留下的印象,这个印象在情感和心理上是浑然一体的,潜存着,激发着,并持续发酵着。 社会性。地方感同时也是对一个区域社会的情感反映,包含着对这个特定区域人群社会的熟悉、融合和认可,自我个体与社群整体相互呼应,紧密联系,有着共同的生活内容和价值观。 文化性。地方感所含蓄的文化性,是说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必定给人以强烈印象,既有特殊的审美成分,又有教化认知的成分,显示出个性魅力。 生物性。地方感是一种特殊情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审美情感,它是以人的生理生物内涵为基础的,如对声光气色的感受,对自然景观和文物资源的情绪反应,都有着生理和生物基础。犹如古代诗人的登高伤怀、暮色生愁,因地理位置改变和时令变化,引起强烈的情绪性反应一样,都有着生物生理的成分在内。 可以分析一下宜春人的地方感。历史以来,宜春人对宜春的自我感觉是不错的,主要是就物阜民丰、风调雨顺来说的,自感山水好、物产好、气候好、灾乱少,特别是古诗赞誉:“我行宜春野,四顾多奇山。”“宜川三月水东流,秀出江南二十州”等等,更增自豪感。同时,宜春不仅自然景色好,而且城乡独具特色,民间概括“东门笋,南门塔,北门秀江桥,西门绣花楼”,地域特征跃然纸上。有词赞之:“南岸柳,北岸樟,化成岩下流秀江。大北门,古城墙,一架浮桥碧水上,袁山春台两相望。”又进一步具象化了。从这些诗词俚语中,可以看到地方感中透出的自得感和怀旧感。犹如上高人说“看不见蒙山就会掉眼泪”,充满着对上高乡土的挚爱和乡愁。而宜春人则以这些乡土特征为情感元素,时时观望着、怀旧着,执着的热爱和眷恋。无不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环境心理,自我欣赏,自我储存,自我扩散,成为定律。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一些较大规模的文体节庆活动在宜春的开展,如江西省第十届运动会,全国第五届农民运动会,已经八届的月亮文化节,加上城市化的迅速升级,新的地方因素不断涌现。有大型的体育场馆,有新建的高楼大道、公园亭阁,有成规模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是明月山的深度开发、温汤硒泉的成功运作,宜春的形象与知名度已异于过去,不同凡响。宜春人此时的地方感,其整体性更为丰富了,社会性更为深刻了,文化性更加厚实了,生物性所决定的社群品味更高了。地方感也就更强烈、更具冲击力,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发展趋势和更自觉的维护意识和自豪心理。 2、地方感的产生 地方感的产生,实质上也就是人们一种特别的情感和心理的形成。从过程分析看,地方感在构序上有一个培育、滋生、积淀下来的逻辑流程。 具体看,一个人出生并在一个地方成长,或一个人较长时间相对固定地生活在一个地方,他就必然融入并熟悉当地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生活,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习惯者和爱好者。比如说,说着和大家一样的方言,吃着和大家一样喜欢的食物,稻米、麦子或畜群的制成品、饭、面包和牛羊肉。穿着同样风格同样质地的衣饰,享受着这个特定地域(不同气候、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家)带给人们的全部资源,如历史、文化、风景、动植物、民俗、食饮、土产、教育、精神性格特征等等。当然,这种融入和熟悉需要较长时间的滋养,从而在特定地域的背景下,逐步建立起个体的生活圈、工作圈、朋友圈以及所有的关系圈,视当地为家乡或者第二故乡,由此形成有浓郁地方色调的情感心理。 融入并熟悉,是形成地方感的重要方式,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这个唯一途径造成的情感心理,又因为其他因素的参照,逐渐深化并固化。主要有两个参照: 第一个参照是距离。美学上有句话叫“距离产生美”,地方感亦如此。在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人群是流动的,但即便在封闭型的古代社会,人群也是相对流动的。当然,流动是相对特定地域来说的。人地关系既固定,又不定。一个人或一群人,都会有可能在一生中,多次或长时间离开融入并熟悉的特定地域,到外面的世界去工作、出差、办公、旅游、居住。这种暂时或永久的脱离,必与其长期生活过的地域产生或远或近的距离。这种距离会让他或他们的故乡留在记忆和情感深处,任何印记或信息,如照片、文字、影视、交流、会见乡人,都会唤醒这些情感和记忆。自觉或不自觉,这些对于故土的情感记忆,都会一次次的唤醒后,发酵成更丰富更深刻的“乡愁”,出现“谁不说俺家乡好”的骄傲心理。这都是距离作为参照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参照是对比。距离是空间隔离造成,但无论有无距离,人们通过对外地域的观看,会对家乡持有一种对比心理。此地与彼地,孰长孰短,孰优孰劣,通过对比进一步认识家乡,深化情感。当然,人伦孝亲,人情喜熟,人的自然本性中,会对长期融入并熟悉家乡,持有明显甚至强烈的倾向性情感,此即“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倾向性情感,是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感情动力,更是爱国文化的源泉。 如果说,熟悉并融入家乡是认同的开始,通过距离产生对家乡的“乡愁”则是依赖的开始,而对比,更是把自我个体的家乡故国情怀,推进到一个更高境界,产生对家乡故国的归属感。 乡愁情愫和归属心态,在一个特定地域的社会人群中,或者说,在他们的文化中,会出现一些有个性的人文意象或文物意象,永远保留下来。 从古代到现代,多少文人与诗人,对宜春山水的赞美,留给宜春人民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让宜春人民更加骄傲自豪。这些精神遗产中,秀江、化成岩、状元洲、文笔峰、袁山、春台、珠泉、北门、岭下、上下水关、鼓楼、下街、青石路、大成殿、箭道、考棚,以及郊外云谷飞瀑、仰山积雪、湖岗台、蟠龙寺、栖隐寺、邓表峰,通过无数文章诗歌的反复咏诵,成为各自独立的文化意象。在这些文化意象中,包含了多少乡愁情怀,多少怜山惜水,多少乡野市雅,是不难体会,不难表述的。在当代作家屠岸、杨佩瑾笔底,就通过对碧绿秀江、如烟如梦的化成岩的描绘,表现了这种人文意象。一个匆匆过客尚如此,久居其境的宜春人,又当如何呢?! 3、地方感形成的基础 从环境心理学角度观察,地方感实际上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是理性的,更是感性的。如果说人与人的情感是地方感主体,则特定地域是地方感的客体。主体作用于客体,才能产生地方感,这是不移的事实。作为地方感的客体,有哪些构成因子呢,值得分析与探讨,借此深化我们对地方感的认识。 自然地理。这是构成一个地方感或地域的主要元素,包含有经纬度,气候,季风,山体,平原,河流,湖塘,土壤,动植物,矿藏,森林乃至天色。即以山而言,宜春境内有九岭山脉和包括明月山在内的武功山脉,其中的仰山、太平山、官山、五梅山,都是佼佼者。两条山脉所孕育的潦河、锦江、袁河水系,则更是滋润此方水土的母亲河,成为生命之源。在长江中下游,类似地域大同小异,但宜春地域却必然以其独特构成,别具一格,著称于世。 街区村落。千百年来,出于生存和便利农业、交通的需要,人类的绝大部分都是逐水而居,拓土谋食,逐渐形成村落和城镇街区。城镇街区是人群相对集中的社会区域,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而村落则是较小的人群聚居地,更突显血缘、宗族的特征。这在中国尤其如此。一定地域的文化特征、文明特征,往往在街区村落集中体现,成为地方感的重要内容。比如袁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就在《天工开物》中较为明显的展示出来。其流域的两座府城,宜春和临江,即袁州府和临江府,无疑集中体现了该流域或该流域的各社会文化特点,成为历史标记,也成为袁州人和临江府人的标记。奉新上高,抗战时曾以繁荣被称为“小南京”,至今声名不减。袁州寨下,以尚武霸蛮闻世,至今亦为人瞩目。此即为浓烈的地域特征,成为上高人或寨下人的标记。 方言。一句家乡口音,顿使游子感慨万千。方言是地域人群的代表性符号,是“亲不亲故乡人”的身份证明。因此,方言往往成为识别性标志,是地域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方言代表着乡情乡俗乡气,沉淀了千年的文化血液和人文基因,更是地方感的重要内容。宜春方言分属赣方言的宜浏片和昌靖片,亦含客家方言,既相异又相通,既陌生又亲切,互相渗透甚至融合。特殊的语音和语法,外乡人不易掌握,成为宜春地域的显著标志,是宜春地方感的要素之一。 民俗乡风。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地域人群的社会演进和生活积累,自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以民俗言之,婚丧寿乐、年节庆忌、敬神驱鬼、人情礼数,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以民风言之,耕读传家、重农轻商、尚武崇文、或蛮狠嗜斗、好讼轻义,也是一方风气,积久成习。这必然形成一定地域人群的主体性格和精神风貌。宜春是吴楚古文化的相逐相融之地,楚文化的鬼神巫蛊和吴文化的尚文好商,皆聚集一地。故既有安土重返、耕读并举的传统,也有好勇霸蛮的巴楚风骨。此外,重视宗族,立祠开堂,年节祭祀,乡规民约,书院私塾,族产助学,庙会戏班,走艺传唱,龙灯龙舟,寻亲访友,皆独具风情,色调浓郁。成为地方感中最令人悸动、思咏不已的乡风乡情。 食品用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往往成为地方象征,非常个性化,唯一性,产生不可替代性,与地方共生共有。袁州的夏布、擂茶、红薯丸子、油茶,万载的百合、爆竹,宜丰的棚户、土纸,樟树的药、酒、盐,几乎是这些地方的代名词。积多少年滋养而成,是一方百姓的创造和宝物,也是物产优势和心理优势,我有你无,或我优彼劣,镌进历史记忆,沁入民众情感,挥之不去,念之不已,睹物思情,有一思百。因之,地域性土特产品,经常超越物质的意义,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地方信物,缺之不可,增之不能,以其本土型,独创性,升级到人文境界,作成地方感的重要内容。 血缘宗族。原始社会裂变后,男性为主的血缘接续成为农业社会与封建宗法社会的支柱,各地域遍布着各种姓氏宗族,聚族而居,农耕传世,血缘联系紧密,与区域社会血肉相联。近代以来,旧体制崩溃,新思想蜂起,社会变革激烈,血缘宗族与姓氏意识淡化,联系松弛,彼此相忘于江湖。改革开放后,宗族姓氏继续稀释,但文化寻根意识加强,各地纷纷修族谱、建祠堂,组宗亲会,寻根问祖,宗亲联谊。从文化的演变流转着,血缘宗族观念有所刷新或流布,是地方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的文化补充。如袁州大姓袁刘易彭,宜丰望姓熊蔡胡漆,皆有动作,是地域人群强化地域意识的一个来源。同时,各地域的各姓氏人群,不论内外,都在地方宗族血缘中,找到自己的世系血脉,寄托一份独有的情愫。 地方人物。每个地域人群,历朝历代都会出代表人物。他们是地方的精英,人人仰慕,成为标杆。人才出现的频率高低强弱,成为该地域兴衰旺淡的标示。袁州晚唐后不再出现人才潮,是历史之谜。但宜丰的陶渊明,丰城徐稚、熊佛西,万载龙榆生,奉新宋应星,高安刘恕,却能永葆影响力,说明文化人物的生命力超过军事政治人物,才学人物越过权势人物,道德人物超越功业人物。由此成为地方骄傲,渗透地方感。 特殊资源。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有特殊资源,但有特殊资源的地方必定为人称誉,甚至名满天下。所谓特殊,就是唯我独有,别人必无。袁州的钽铌矿、硒温泉,就是如此。容易识别的是特征,不能忘记的也是特征。历史文化资源更是这样,如樟树的吴城遗址,高安的元代青花瓷,奉新的百丈清规,袁州古天文台,铜鼓秋收起义策源地,上高会战遗址。文物往往成为怀旧与乡愁的信物,或睹物发思古之幽愤,或见迹生岁月沧桑之惆怅,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寺庙、墓葬、城墙、古桥、塔楼,如袁州的文笔峰、湖岗台、状元洲、化成岩,深深的锲入袁州人的心灵,永远不能淡去或消失。 4、地方感价值分析 地方感的构成有三个成分:人(自我主体),物(地域物象即自然客体),情(精神心理)。 试从价值层面予以分析:人是自我主体,物是自我客体,情则是自我主体作用于自我客体后,所产生的自我主体的精神心理。自我主体是第一存在,是地方感的核心存在。自然客体则是第二存在,是地方感的辅助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意识就是属于自我主体的精神心理。 自我主体之于自然客体,有着绝对意义。主体不存在,客体无意义,精神心理更无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自我主体的绝对性。 同时,自我主体作为第一存在,作用于自然客体和精神心理,必会发生三个不可不回答的问题。 a、我从何来? 此问题的解决还须先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我是谁”并非是个玄学问题。从根本上看,“我是谁”与“我从何来”同义。从哲学层面看,人类生生不息,其来有自。次第回溯,人来源于宇宙天地,是物质的转换。“我是谁”曰:“我”是自然一份子,物质也。“我从何来”曰:从物质世界来。从事物运动变化的逻辑看,“我从何来”的何处,就是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的一个局部,即某地域,袁州,万载,或上高等等。 b、我在何处? 这个问题简单。如上所述,“我在何处”,即此时所处,某地某城某乡。自我主体在何处,即为何处人,宜春人或南昌人。当然,生长在某地并成长在此,如宜春或南昌,叫宜春人或南昌人。虽然后来离开了此处,他的籍贯依然为宜春或南昌,身份的明确往往就是自我主体的明确,同时也是精神心理的明确。 c、我往何处去? 此问题较复杂。“往何处去”并非现实世界的“人往高处去,水往低处流”,迁徙、旅行、寻路、去之有向,向之可也。此只是自我主体的移动,或暂时,或长久,甚至永久。“我往何处去”实质上问的是一个精神归宿问题。没有必要进行玄学或神学的探讨,例如牧师或禅师会告诉你,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情景。中国人敬天法祖,效忠土地,精神情感的归宿往往在实用理性的角度上,自然选择到现实世界予以寄托。是何处人就会情感流注到何处。此处此地即是“何处”,也就是自我主体和精神主体的归宿地。“我”是何处人,自当往何处,这就是答案。 这三个问题,说的是生命世界与非生命世界的对立与统一。是自我主体时时疑惑又必须明确的问题。在地方感的范式内,这个明确须如上所言。 再进而言之,自我主体的生命与灵魂,即主体与主体精神,又会产生AB两个现象系列: A是自我主体的生命系列。其走向是:生命个体之所由来→生命个体自始至终的生存经历,也即人生经历→生命个体在生命群体之中的位置,即其社会关系(亦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B是自我主体的精神系列,其走向是:我(自我主体)→家(自我主体所处的婚姻血缘客体)→家乡(自我主体所处的社群客体)→家园(自我主体所处的民族国家客体)。 A系列证明了自我生命的存在意义,是生命感的依托和延续。B系列是自我命运的存在意义,是自我生命的展开与依附。生命感与命运感,是地方感精神心理的核心部分,也是其价值所在。 自我主体的精神生命之放射,在宜春历代文人中比比皆是。 晚唐权相李德裕贬到袁州,失意零落,却绝不屈服。他在宜春写《山凤凰赋》以自况。山凤凰(一种类似山鸡有着漂亮羽毛的禽类动物)珍惜羽毛,宁被射杀,也绝不乱飞乱撞以保持尊严,李对此予以赞美。袁州状元卢肇则在被夺官职后,写《震山岩记》抒其隐居震山,与水为邻,日与友人狩猎吟诗的闲适心情,掩盖内心怀才不遇、失望怨愤的情绪。李德裕“羽毛自惜”,宁杀不辱,有气有骨;卢肇以震山游溪为志,追求自我放纵的闲适,都是其精神生命的特殊表达,令后人咏叹和追慕。 郑谷的《鹧鸪诗》,其乡愁表现得更为深切,“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为何如此?是因为久居此地的鹧鸪“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游子的乡愁,文人的惆怅,掺和着人生沧桑和命运的惆怅感,细细流入感悟着的心田。李德裕、卢肇、郑谷三个宜春历史名人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命运,展示了自我主体与精神主体的绝对意义。 5、展望与结论 对地方感研究的兴趣,不是个别或局部现象。西方学者数十年来的探讨,为地方感研究穿上了各种理论外衣,我们应予注意,不应盲信。 东西方人类的地方感,当然有共通性或相似性。如眷恋家园,寻问祖源,寻觅家族流转播迁的文化脉迹等,兴趣指向基本一致。但相异处不少,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作为大陆民族,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更高,生存与土地几乎融为一体。观念上极敬畏祖宗的权威,对血缘伦理特别看重,强调社会的稳定性、不易性。对土地和祖宗的地方感,表现出特殊的情怀。 我们还可以放开视野,作更为深入的观察。 原始社会解体前,起码在六千至一万年前,人类的地感是不存在的。那时的人类在地球上是不断流动的,或渔猎,或采摘,或游牧,逐食而居,不断迁徙。直至进入农耕社会,人类的物质生产和自我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化,这才有了人群的定居,王国城镇村落才可能诞生。定居变成久居,人类身份发生重大变化,地域开始成为身份象征,开始以中国人、朝鲜人、印度人互称,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也开始以中原人、江南人、两广人或云贵人互称。地方人与地方感同时产生。 事情并未停止。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又开始发生较大规模的流动播迁,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市场化,羊吃人,宗教战争,发现新大陆等等,人口的增减流转,令人目瞪口呆。但是,不管何种民族,也不管何种文化,动变中的人类,无一不亘古不变地寻找着他们的精神家园,与地方感的出现扭成一团,撕掳不开。 但新的因素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生态环境的恶化,促成新的生态观念的成型;人类新的信息和人际交往方式的出现,比如说互联网,造成新的文化体系和新型观念的出现;在生活理念与交往方式完全更新的地域,新的人际社群正在出现。新哲学,新体验,新精神,新趋势,蜂涌而来。这一切,为地方感注入无穷多的新鲜血液,新的时代来临了。但是,人们会惊讶地看到,人类在精神深处,积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沉淀下来的核心情感,那种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对生命归宿的叩问,对命运浮沉的探究,始终没有停息下来,仍然不可遏止。 地方感的进一步研究将在这个背景下继续展开,我们提示这一些,是想揭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地方感中的核心理念是不可逆转的。 文/刘密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