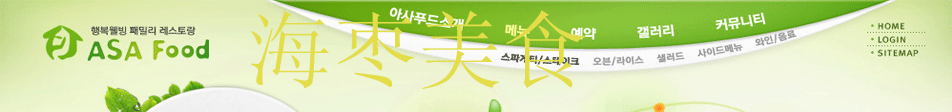|
两汉霸陵县(邑)是长安城东郊的近县,境内有诸多重要的陵墓、祠庙、离宫、关梁,政治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该县原为秦芷阳,后因汉文帝在此县境内白鹿原上修筑陵墓而更名“霸陵”,《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文帝九年(前),温室钟自名。以芷阳乡为霸陵”,霸陵邑由太常直管,汉景帝前二年(前)薄太后葬于南陵,遂将南陵从霸陵邑中析置出来另置南陵邑。汉元帝时下诏诸陵分属三辅,霸陵邑归京兆尹管辖,新莽天凤二年(15)改名为水章县,更始元年(23)复名霸陵县,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撤南陵县并入杜陵县,曹魏正始五年()改为霸城县,“霸陵”县名遂废,前后共计沿用年。对霸陵县(邑)界的研究可追溯到清代乾隆时期,《咸宁县志·历代疆域图》:“大抵自白鹿原以北至渭皆秦芷阳(汉霸陵)地”,并附有地图示意。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王社教《汉长安城的闾里》、刘振东《简论汉长安城之郊》等文中也对县界有相关论述,但并无专门、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本文拟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地形地貌及考古材料,对两汉京兆霸陵县(邑)四界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促进西安灞桥区史地相关研究,不到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界变迁概述 霸陵县(邑)东临新丰、西邻长安、南邻杜陵蓝田、北邻阳陵高陵,汉初县界与秦芷阳基本一致。在汉景帝时南陵邑从霸陵县(邑)析置出来,到东汉时期省入杜陵县,导致南段县界略微北移动,不过县域大体格局基本稳定不变。自曹魏时更名霸城县以后辖地逐步变迁,尤其是南北朝时县域南部变化较大,霸城县南邻的杜城、山北、白鹿等县是在汉代蓝田县、杜陵县、霸陵县基础上改置而来,各县之间多有相互交错的“飞地”存在。至北周明帝时在长安县东部另置万年县、武帝时废霸城、杜城二县入万年县,此举彻底破坏了汉代以来的霸陵县(邑)境域格局。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四界考实 东界:霸陵县(邑)东部辖地有“霸川之西坂”,《三秦记》载:“白鹿原东有霸川之西坂,故芷阳也。”今灞河以东、临潼骊山芷阳沟以西台塬即“霸川之西坂”,又称铜人原。原上有秦东陵、高坡、井深沟、洪庆、刘家底街子、向阳公司等多处秦墓群,经历年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带有“芷”字陶文的陶器,表明墓主为秦芷阳县居民,直接证明文献所载属实,铜人原一直是秦芷阳、汉霸陵县(邑)辖地。铜人原北边缘在今临潼芷阳村——洪庆村——西张村——代杨村——灞桥吕家堡一线,此即霸陵县(邑)东界。在铜人原西北有汉成帝废昌陵(今临潼斜口窑村),属汉新丰县戏乡辖地,又按《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所载,废昌陵以北仍为霸陵县(邑)所辖,此段县界在临潼西渭阳村(坐标N34°26′50″,E°08′54″)——魏庄村——坡底村——贾村——高家村——郭王村——温家寨至铜人原北边缘一线,废昌陵所在地新丰戏乡凸入霸陵县(邑)境内体现了“犬牙相制”的划界原则。铜人原东南是骊山/蓝田山,《汉旧仪》载:“骊山者……此山多黄金,其南多美玉,曰蓝田,故始皇贪而葬焉。”按其所载,骊山南麓在秦汉时期名为蓝田山,属于蓝田县辖地,可见铜人原与蓝田山、骊山分属霸陵、蓝田、新丰三县所辖,铜人原东、南边缘在今临潼杨寨村——北沟村——土地凹——灞桥马坡——吴家坡——郭李村——安家庄(坐标N34°1517",E°833")一线,此即霸陵县(邑)与蓝田县交界,再往东便进入蓝田县“蓝田山”山区。铜人原西是白鹿原,在这两个台塬之间灞河呈东南——西北流向,俗称“蓝田川”,《三秦记》载:“蓝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铜铁石。”按其所载,“蓝田川”属于蓝田县辖地,故此霸陵县(邑)铜人原以南(今灞桥区安家庄)是以蓝田川(今灞河)为界。至于铜人原以南、灞河东岸华胥镇昭襄王陵和泄湖秦墓两处与秦芷阳有关的遗迹,今已证明与芷阳县无关,恕不赘述。 北界:《水经注》载:“《三辅黄图》曰:秦造横桥,汉承之,置丞,立石柱,柱南,属京兆,柱北,属右扶风。各分其半。”按其所载,汉代京兆尹(郡)北界是渭河,隶属于京兆的霸陵县(邑)北界同样也是渭河。不过汉代渭河故道绝非今日渭河的河道,渭河在历史时期的变迁以北移为主要趋势。近年发现的秦汉时期“渭桥”对长安城、霸陵县(邑)以北的渭河故道具有指示作用,年在西安市北三环外西席村、高庙村北农田两处挖沙坑中暴露了两座秦汉古桥。西席村北古桥正南为汉长安城“厨城门”,故被称为“厨城门桥”,高庙村北古桥正南为汉长安城“洛城门”,故被称为“洛城门桥”,后又在西安未央区草滩镇王家堡发现秦汉时期古桥,命名为“王家堡古桥”,因正北与阳陵、阳陵邑相对,故推测为汉景帝所建的东渭桥。可证秦汉渭河故道在未央区席王村——高庙村——草店村——王家堡一线,至西安警官职业学院浐灞校区附近与灞河相汇。在灞河以东的高陵耿镇有唐代东渭桥遗址,且附近有秦汉时期墓葬和遗址,推知渭河在灞渭交汇后沿着灞桥区南草甸——马家堡——耿镇一线东流。按《水经注》:“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帝更修之”所载来看,曹魏时期仍在中渭桥原址附近重建渭桥,可见秦汉至曹魏时期渭河中游河道并未发生过大规模变迁,汉代霸陵县(邑)北界一直是秦汉时期的渭河故道,在今未央区席王村至高陵区耿镇一线维持不变。 西界:陵县(邑)西临长安县(长安城),原为秦咸阳长安乡,汉高帝五年(前年)始置长安县。对此段县界,今学者在汉长安城郊相关研究中多有论及,王社教《汉长安城的闾里》:“汉长安城东门及其城墙即为长安县界。”刘振东《简论汉长安城之郊》“(长安县)东郊与霸陵县为邻,大约以灞水为界。”霸陵县(邑)境内有枳道亭和霸城观,均位于灞河以西,《后汉书·郡国志》:“霸陵,有枳道亭。(集解)苏林曰:亭名。在长安东十三里。(索隐)云:枳道亭东去霸城观四里,观东去灞水百步。苏林云:在长安东十三里也。”此处“长安东”是指长安城东。西汉时期枳道起点在汉长安城宣平门,“枳道”从汉长安城宣平门起始向东经灞桥(今灞桥区段家村秦汉灞桥遗址)后东出函谷关,枳道亭距长安城宣平门十三里(约5.4公里),推知大体位置在今未央区团结村(坐标N34°20′38″,E°58′25″),霸城观则在枳道亭东四里,紧邻灞河西岸。由此可见长安、霸陵两县交界即非灞河、也非长安城墙,而是在二者之间。从文献记载来看,《水经注》载:“霸水又北迳枳道,在长安县东十三里,王莽九庙在其南。”此处“长安县东”指长安县(东)界以东而非位于长安城内的县城以东。按其所载,霸水和枳道相交处在长安县(界)以东十三里(约5.4公里),今长安城宣平门遗址至灞河二十里(约8.4公里),反推可知长安县东界距城宣平门七里(约3公里)。若按《汉书·百官公卿列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皆秦制也。”的理想状态来看,每个亭占地约四平方公里,从枳道亭向西五里(约2公里)也在城东七里(约3公里)处。所以“(长安)城东七里”就是长安、霸陵两县交界。从秦墓分布规律来分析,在西安北郊秦墓集中于北康村、尤家庄、凤城三路、张家堡等地,经考古发掘后出土大量带有“咸亭某里”字样陶器,墓主显系葬于此地的秦长安乡平民。自“城东七里”的魏家湾往东便再无秦墓分布,按照平民生于本县葬于本县的规律来看,未央区魏家湾一带(坐标N34°20′52″,E°58′25″)当为秦长安乡、汉长安县东界;西安北郊地势较为平坦,汉长安城东城墙并无曲折,霸陵县(邑)西界当与城墙平行,自魏家湾直向北延伸至秦汉渭河故道,即今未央区魏家湾——河址西村——吕小寨——韩家湾一线,韩家湾(坐标N34°23′11″,E°58′25″)是霸陵县西北界点。在枳道亭西南霸陵县(邑)与奉明县(邑)相临,此县由奉明园益户形成,而奉明园又来自于地名“广明”,是长安城之东的郭城门,说明奉明县(邑)是从长安县中析置出来的。在汉长安城广明东都门附近还有广明苑,即史皇孙与王夫人葬地,《汉书·武五子传》:“史皇孙、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苏林曰:苑名也。”又因为长安城郭城门均设置有外郭亭(即小城),所以《武五子传》又载:“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位于西安北郊的史皇孙刘进夫妇墓(又称王夫人墓)今已辟为文景公园,东距汉长安城墙约1.38公里(汉代三里),广明亭在其南临,现按“十里一亭”的规律测算,文景公园往东五里(约2公里)未央区凤苑新区当为奉明、霸陵两县交界,该地正北三公里恰是魏家湾。在刘进夫妇墓东南、枳道亭正南是龙首原,呈东北——西南走向,原上汉墓极多且大多经过考古发掘,不过土器物上未见有表示地名的文字,故此只能从墓葬群的时空分规律来推测。位于龙首原大明宫区域汉墓群与长安城联系紧密,年代多在西汉早中期,再向东则有约三公里的空白地带,至光大门黄土梁、辛家庙洼地才出现分布较为集中的汉墓群,年代多在西汉晚期与东汉时,可见这两处汉墓群应是不同城邑聚落居民死后聚族而葬形成的。靠近汉长安城的大明宫区域汉墓群隶属于长安县,而靠近灞河的光大门、辛家庙区域汉墓则隶属于霸陵县枳道亭,在两处墓葬群之间的空白地带就是县界,今未央区井上村——八府庄——三府湾一线。在龙首原南麓有六条余脉由东北至西南,分布于今西安城北红庙坡与南郊的大雁塔之间,称作“六坡”,位于六坡上的秦汉墓葬多被唐长安城遗址破坏,但也并非无迹可寻。今新城区长乐东路韩森寨有韩森冢,墓冢位于长乐坡中心海拔最高处,长乐坡原名浐坂,《太平御览·地部》:“《西京记》曰:浐水西岸有阪,旧名浐阪。隋文帝恶阪之名,改名长乐坡。”民间传说该墓是秦“庄襄王陵”并有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石碑,年经考古钻探后确定是先秦时期秦国公(王)级别墓葬。鉴于《水经注》明载庄襄王陵在铜人原、庄襄王陵的说法又起源于宋代,所以墓葬主人绝非秦庄襄王,今学者推测可能是悼太子或孝文王,无论是哪位秦王,按《史记·秦本纪》所载均为“葬芷阳”。结合秦公(王)陵墓独占台塬的建置规律,长乐坡整体属于芷阳县,台塬西缘八仙庵——西交大——沙坡一线当为县界。 南界:韩森冢南部是乐游原,台塬呈西南——东北走向,长约3.5公里、宽约~米,最高处在铁炉庙北侧。乐游原最初是秦杜县宜春苑的一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西汉称宜春下苑,包括今日乐游原和曲江池,宣帝时改称乐游苑并兴建乐游庙,《汉书·宣帝纪》:“三年春,起乐游苑。师古曰:《三辅黄图》云在杜陵西北。又《关中记》云宣帝立庙于曲池之北,号乐游。案其处则今之所唿乐游庙者是也。其馀基尚可识焉。”按《长安志》所载乐游庙在唐代“升平坊”内,今经考古调查确认乐游庙遗址在今雁塔区观音庙。可见乐游原整体属杜陵县(邑)所辖,台塬北边缘沙坡(坐标N34°14′41″,E°59′30″)——医院——张家坡——韩森东路/浐河西路口(坐标N34°15′39″,E°02′17″)一线即为县界。乐游原南、白鹿原西是杜东原,汉宣帝杜陵位于杜东原北部,《汉书·宣帝纪》:“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今经考古发掘发现秦汉时期属于秦杜县的马腾空秦墓、属于汉杜陵县(邑)的三兆村、马腾空汉墓均不过浐河,表明浐河是杜陵邑与霸陵县(邑)交界,浐河以西属杜陵县辖地,浐河以东的白鹿原属于霸陵县。按《关中图》:“白鹿(原)在霸陵。”不过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括地志》、《长安志》等文献相关记载可知,白鹿原并非全部属于霸陵县(邑)辖地而是分属霸陵、南陵、蓝田三县,其中霸陵县辖地在北、南陵县辖地居中、蓝田县辖地在南。世传汉文帝霸陵位于今灞桥区毛西村凤凰嘴,后经过考古调查以后发现此地并无汉代遗迹,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汉文帝霸陵。江村大墓整体位于一个独立台塬上,在陵墓南、北部各有一条东南——西北向自然沟,南部自然沟起自金星村止于神峪寺沟,北部自然沟起自任家坡止于唐家寨,霸陵与窦皇后陵均位于两沟之间。按照秦汉帝陵独占台塬及文物遗存分布情况看,这两条自然沟即霸陵的陵园南北界。而薄太后南陵作为有别于霸陵的独立陵园,单独位于江村南部的自然沟以南。东汉时期南陵县(邑)并入杜陵县以后,江村南部东南——西北向自然沟便成为霸陵、南陵两县交界。南陵县(邑)有沂水,《汉书·地理志》载:“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沂”为“浐”之误,沂水就是浐水,又名长水。浐河由上游汤峪河、岱峪河、库峪河、荆峪沟等几个支流汇成,其中荆峪沟(鲸鱼沟)发源于今蓝田县白鹿原荆山西麓的毛家十字,在高桥附近注入浐河,流向为东南——西北向,又称荆溪或直接别称为长水。秦汉魏晋时期认为其是浐河主源,《水经注》载:“霸水又北,长水注之,水出杜县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谓之荆溪。”荆峪沟(今鲸鱼沟)将白鹿原斜切分割为南北两个小型台塬,北部称为狄寨原、南部称为炮里原。汉文帝霸陵、窦皇后陵和薄太后南陵均在狄寨原上,而秦汉时期蓝田故城则在炮里原上,《长安志》载:“蓝田故城,在县西三十里(约14公里)。”按距离推算在今蓝田县留村一带,可见荆峪沟当是南陵县(邑)与蓝田县之界。南陵县(邑)东南界点是“蓝田谷”,《水经注》载:“《地理志》曰:浐水出南陵县之蓝田谷……浐水又北历蓝田川,北流注于灞水。”此“蓝田谷”是蓝田境南山诸谷之总称,而不是一条山谷。按其所载,浐河源头蓝田谷既属南陵县(邑)又属蓝田县,两县共有的河谷当为县界,蓝田县荆山西麓的毛家十字(坐标N34°453",E°171")即南陵县(邑)南界点。在白鹿原荆山东南、灞河东岸是隋唐蓝田县城(今蓝田县城),《括地志》载:“芷阳在雍州蓝田县西六里。”即从唐代蓝田县城向西六里(约3公里)便是芷阳县界。隋唐蓝田县城即今蓝田县城,从今蓝田县城向西三公里大体在白鹿原西边缘,由此推知白鹿原西边缘(灞河)即为芷阳与蓝田县交界,此段县界自自蓝田县毛家十字向北沿白鹿原西边缘至灞河(蓝田川)。 结语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自文帝九年(前)更名,于曹魏正始五年()改为霸城县,前后共计沿用年。汉霸陵(邑)北界为渭河,即今灞桥区南草甸——马家堡——耿镇一线秦汉渭河故道;东界自渭河向南,绕经废昌陵后以铜人原东边缘、灞河(蓝田川)为界;西界在“(长安城)城东七里”,今韩家湾——井上村——三府湾一线,向南沿长乐坡(浐坂)西边缘至乐游原北边缘,后折向西至浐河,以浐河为界向南至荆峪沟西口(长安区高桥乡);霸陵县(邑)南界原为荆峪沟(鲸鱼沟),起自蓝田县毛家十字止于长安区高桥乡,汉景帝置南陵后以霸陵的陵园南界为县界,即今灞桥区江村南部自然沟,起自金星村止于神峪寺沟一线是为县界。(如图一)整体上看,除东部新丰戏乡(废昌陵)凸入霸陵县(邑)境内属于“犬牙相制”以外,其它各段县界均符合“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